
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缅北及妙瓦底诈骗园区,展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堕落产业链。更可悲的是,当部分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整个系统便完成罪恶的自我繁殖。破解这场伦理危机,须要人们重新定义何为“好猫”,重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藩篱。
据泰国《民族报》报道,1月27日,由中国公安部组成的代表团,到泰国暖武里府会见泰国科技犯罪调查局官员时称,多方情报显示,在缅甸妙瓦底市(Myawaddy)有36个主要由中国人经营的大型电信诈骗团伙,雇佣超过10万人骗取他人钱财。有许多中国公民被利诱或拐骗到缅甸,为这些犯罪团伙工作,部分受害人据说遭到殴打,有些还因此丧命。
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里此起彼伏的哭喊声,像一柄利刃刺破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华丽帷幕。36个主要由中国人运营的犯罪集团,10万被奴役的诈骗从业者,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当“结果至上”“金钱至上”的生存哲学吞噬人性底线,当”白猫黑猫论”异化为道德虚无的通行证,整个社会正在支付难以估量的伦理代价。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民间谚语,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圣经”,也有了一个很好听的简称:“猫论”。“猫论”最早出现于1962年,在中国大饥荒之后,一些农村自发产生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新的生产形式,引起大陆政府党内争论。大陆政府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内部会议讲话,“猫论”并没有传播。
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点名批评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猫论”由此成名,成为邓公的招牌。1978年,当他再次复出,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他认为搞理论争论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自此,“猫论”主导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到特区、证券、股票等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可以说,是“猫论”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中国进入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全新时期。
1985年,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工具理性异化:从发展哲学到道德真空
但是,就在“猫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利益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猫论”也在不断地被滥用。在”猫论”的原始语境里,蕴含着突破计划经济桎梏的革新勇气。遗憾的是,在“唯经济论”浪潮的冲刷下,这种实用主义哲学,逐渐蜕变为功利主义的遮羞布,工具理性也逐步异化。有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以此来掩饰利益驱动下道德、责任的缺失。尤其是当”成功”的定义被简化为银行存款的数字,当”能力”的评判标准窄化为攫取财富的多寡,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于是发生危险的偏移。带毒的食品、各种形式的坑蒙拐骗,很多人用鲜血写就的”成功学”,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异化的极端样本。
近年来渐为人知的缅北及妙瓦底诈骗园区,展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堕落产业链。从中国国内“人力资源公司”的虚假招聘,到境外“园区”的暴力囚禁;从话术手册的情感操控,到赃款洗白的金融链条,每个环节都精准践行着,“抓到老鼠”“搞到钱”这一“结果导向”的生存法则。被骗者沦为犯罪者的“人形ATM”,施暴者异化为赚钱机器,这种双向的人性湮灭,暴露出工具理性碾压道德底线的狰狞面目。更可悲的是,当部分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整个系统便完成罪恶的自我繁殖。
破解这场伦理危机,须要人们重新定义何为“好猫”,重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藩篱。深圳南山区的科技企业用创新定义成功,杭州的互联网公司以普惠改写商业逻辑,这些案例证明,经济发展与道德坚守可以同频共振。当法律长出更锋利的牙齿,当教育重启心灵的启蒙,当每个公民在追逐财富时,仍能听见良知的叩问,我们才能避免让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冲垮人类文明的道德堤坝。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重构。从东莞工厂到中关村咖啡厅,从直播带货间到跨国办公楼,每个经济细胞都须植入道德的基因。只有人们终于懂得,真正的现代化不仅是GDP的狂飙突进,更是人性光辉的永恒照耀,那些困在妙瓦底诈骗园区里的灵魂,或许才能等来真正的救赎曙光。毕竟,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征程上,不能只有黄金铺就的康庄大道,更需要道德铸就的精神丰碑。
中国,是时候重新定义何谓“好猫”了!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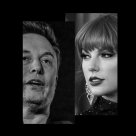 评论: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评论: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印度: 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
印度: 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
 重启核军备竞赛?应对中俄美国考虑扩大核武
重启核军备竞赛?应对中俄美国考虑扩大核武
 工业化奇迹不再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致富指
工业化奇迹不再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致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