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也一样现代化,为什么传统文化气息比中国还浓厚呢?我看,这件事不是败于外部环境,而是败于多年不重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爱国主义情愫的教育与培养,败于自身某种极端思维。
过大年,即使对五六十岁上下的中老年人,也是有些隔膜、淡远的。儿时确有过年味记忆,也有过春节的期盼。那时中国物质短缺,生活乏味,只有过年,人们才能海吃海玩“放纵”一回,孩子还可能有平时难见的糖果饼干吃,有新衣穿,以骄邻家的孩子。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仅带着我们买过一次鞭炮,是那种比小鞭炮声音更大些的中型“雷子炮”,五十个一扎。“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于是也就生发了许多喜气与祥和。春节那几天,随父母逛街市,到处花花绿绿、张灯结彩,亦令灰色单调的城镇平添许多生动和靓丽。
我对春节的印象,较深的是1963年,那时困难时期刚过,经济有所复苏,民间也有了些许生气。于是我们那个山区小城的居民和城关镇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街头店铺前表演起各种节目。有的戴着大头娃娃假面具,随着锣声鼓点,扭起秧歌;有的踩着高跷,在唢呐声中很有节奏地表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或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县城十字街口,是小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夜晚这里挂起汽灯,搭起戏台,县剧团及民间一些团体义务给大家演戏。看戏时人山人海,观者如堵。小孩子只热衷于人群中你躲我藏,打打闹闹,并不像大人那样专心看戏。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小孩子最喜欢的是打着灯笼,竞夸自家灯笼的漂亮精致。
后来,随着当时的“左”风日劲,对年的感觉,就有点一年不如一年了。文革时,干脆视春节亦即旧历年的民间一切欢庆活动为“四旧”,都在横扫之列,故过年除三天假还保留外,已无喜庆可言。有一两年,不知哪位高人,竟还提出“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要求人们节日也不休息,去劳动加班,却终因太不得人心,遂不了了之。
1978年之后,我已成人,心思早不在过年过节的期盼上。春节于这个时代,似乎就是看看央视的文艺晚会,放放鞭炮,睡几天懒觉。有一两年,曾参加过春节期间的同学聚会,本是件雅事,却成了官座相逐,人面高低的“名利场”,于是顿感索然,遂不愿多去。所以对这二三十年的春节,竟没有留下多少美好记忆。
近些年,这样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人们为何却越来越缺少感觉,近于“式微”了呢?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是商业对传统的伤害引起,有人说是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不力所致。河南甚至有大学教授最近发出《保卫春节宣言》。
从心理层面上而言,一些传统佳节不及洋节人气兴旺,窃以为原因有二:一是人们缺少对节的期盼和憧憬。过去物质短缺,一年到头也难沾荤腥,“嘴里淡出个鸟来”,故不只孩子,大人对过节也充满期待。如今生活渐渐好起来的多数中国人,还有这种吃喝的期盼吗?消费主义的浮躁和生存竞争的压力,又使得中国人对新一年的命运难免有种不确定感,降低对未来的憧憬度。失去期盼和憧憬,自然也就年味索然。至于下一代对洋节的情趣何来,因为代沟,不解其详。推测起来,或亦是对西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呢?待考。
农民工之所以每年节前无论如何要赶回去,以至造成春运紧张,说到底,还是因了期盼之故——一年到头难得一次的家人团聚。故,于他们,有期盼,就还有年味。偏偏某些官商又不体恤民情,竟借机在票价上猛涨一把。其忽视春节内心建设之短视,令人唏嘘,更令人遗憾。
二是过节总是和某种记忆相联系的。失去传统,也就失去记忆。如同海外华人归国省亲,寻祖问宗,却发现原本很有特色、千姿百态,和儿时记忆相连的古城镇,成了千篇一律、洋味十足的高层建筑群,于是内心的失落和荒芜可想而知。春节的底蕴是不是也因同样道理而逐年减薄?我说不准。
不管怎么说,传统文化和节日的式微,对一个民族总是悲哀的事情。文化于国家是一种软实力,于民族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居然被韩国抢先一步认定为该国的文化遗产,如果再听任传统文化衰败下去,恐怕春节也会被越南人再抢注。好消息是,去年,春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层面上的“保卫春节”总算成功。
说是现代化全球化对文化侵蚀的恶果,我总是有些疑惑,韩国也一样现代化,为什么传统文化气息比中国还浓厚呢?我看,这件事不是败于外部环境,而是败于多年不重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爱国主义情愫的教育与培养,败于自身某种极端思维。故今日,许多中国人已形成妄自菲薄,盲目崇外的浅薄心理意识,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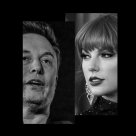 评论: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评论:中美关系需要“马斯克+斯威夫特”
 印度: 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
印度: 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否正在
 重启核军备竞赛?应对中俄美国考虑扩大核武
重启核军备竞赛?应对中俄美国考虑扩大核武
 工业化奇迹不再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致富指
工业化奇迹不再 发展中国家需要新的致富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