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由于一些事情,炒房这一现象又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这不是特例。1979年深圳特区成立,无数人失眠,想着如何去大干一场;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无数人又失眠了,想着怎么去炒一套房。
近年来,中央已经大力提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暴利之下,资本趋之若鹜。怎样从源头上遏制住炒房动机,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可能是深入理解炒房现象背后的运行逻辑。去年,《中国证券报》曾在三省进行过调查。现将该文推荐给大家。
记者手记:如果不是这几天的采访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无法相信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简单而暴利的商业模式。
下个月,我的采访对象魏广华(化名)就要离开Z市了,寻找下一个猎物。在他的“团队”进驻Z市的9个月里,这里的房价高歌猛进,他带来的2000万现金,也只花出去了1000多万,现在卡里一共躺了接近5000万现金。
“炒房要的是够准够快够狠,无异于刀口舔血,狠赚一把就要离场,寻找下一城。”很难想象,作为楼市炒家中的新兵,魏广华的捞金速度竟如此之快。
下面,是记者再现的三个城市的炒楼故事。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中,有的人暴富了,更多人的未来被房子裹挟,艰难前行。
1.A市“坐庄”风云
“9个月时间,均价涨2倍,个别楼盘超过3倍。”尽管位于东南沿海省份的A市极为重视清明节,但魏广华(化名)却“舍不得”回家祭拜先人,“联手坐庄”这种在股市里操纵市场的方法,被他和几个炒房兄弟,娴熟地“嫁接”到房产领域。
“以前做实体经济,成日操心操肺劳神苦思,但是房地产不同,只要你将局部的东西理解透彻,资金流不要出问题,就躺在家里赚钱了。这种四五线城市,前期政府不仅不会干预,反而非常欢迎房价上涨。”魏广华头头是道。
回想起来,魏广华自称“如入无人之境”。2016年中,隔壁B市岛内的均价已经突破4万元,与其比邻的A市才六千多块钱。短短9个月过去,A市新楼盘开盘价鲜有低于每平米1.5万元的,个别湖景、江景、学区房,甚至在2.5—2.8万元之间。
“A市区有两片旧城拆迁,以及6个自然村要征迁。这些拆迁户大约1.5万户,平均每户至少握着百来万拆迁补偿款,此刻拉升房价,不愁没有接盘侠。均价低、流通盘小、有旧城改造的刚需,配合一点学区房的概念,是个很适合讲故事的地方。”
到A市安营扎寨后,魏广华首先相中当地名校某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彼时该小区均价约为1万元。这是个典型的“学区房”二手盘,小区内“流通盘”不到50套,介于60—80平米之间,只需不到1000万的资金,便可一把吃下“流通盘”,这就相当于控制住了该盘近乎全部的流通市场。
这一“套路”屡试不爽,他们如法炮制,陆续在市区扫掉接近500套小两居,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于A市二手房交易市场的三分之一存量,花费则不到1亿元。仅仅三个月,A市的房价已在刺激下,每平米涨了近2000元。
“十个人要一口气买下这些房子不是易事,毕竟树大招风。因此,上数量级的投资,就得从老家亲朋好友那里借来身份证。此外,他们还通过中介公司找农民工买身份证,通过各种渠道开具收入证明,甚至拿到贷款优惠。”魏广华说起如此“简单又暴利的赚钱方式,感觉有点上瘾”。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找到在当地有一定规模和垄断地位的房产中介机构合作,开始刷新手中房产的挂牌价格。与此同时,通过媒体、论坛等途径,为“A市B市同城化”、学区房、江景房等概念造势。
加之旧城改造和自然村拆迁形成的刚需,以及临近地级市的土豪纷纷赶赴这里扫楼,这个曾偏居一隅的四线农业城市,在市区人均收入约3000块钱的情况下,市区房价却以近乎“一天一价”的态势,从六七千元起步,向1.5万元、2万元、2.5万元、2.8万元进发。
2017年4月初,魏广华在宾馆见到记者时,满面春风。他说这辈子从未想过有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
2.基金经理“结伙”赴H市
胡英杰(化名),炒家,2015年“股灾”之前,他是一名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基金经理。自股灾“败光”之后,他的主营业务从炒股变更为炒楼。
“相对于琢磨不透的股市,楼市风险更小,利润更高,更易于把握。”在胡英杰看来,“最核心的是运用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股市的杠杆太低,买多少股票,你就要投多少钱,但H市(西南某市)的话,我现在投个30万块钱,可能就可以把一个100万的房产买下来。买下来可能过不了多久就翻倍了,这个时候的收益率一下就放大4倍。”
“在此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2015年1月份在深圳购入一套价值300万元的房子,该房产现在市值约900万元,收益高达690万元。如果同时段将购房首付90万元投资于股市,到如今能保本已算万幸。”胡英杰表示。
那么, 胡英杰这回为什么会盯上H市呢?“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H市某小区,该小区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盘,是亚洲最大楼盘,占地1830万平方米,计划入住人口50万人”,他说。
从今年1月初开始,胡英杰在该小区租下一套房,白天要么到市内中介门面串门,要么在家做功课,对比H市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差距,并试图寻找原因。但是,晚上9点过后,胡英杰们都要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一栋栋楼排查入住率。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简单,在楼底下挨家挨户数电灯,并认真做好笔记。
经过三个月的调研,胡英杰基本摸透了,该小区的入住率已经达到80%。这个“神盘”的入住率是炒家评判H市是否值得一炒的主要指标。
“你知道吗,H市竟然还没有地铁房的概念。”胡英杰说,按照他过去两年在深圳积累的经验,两条地铁线交汇处的房价涨得最快最凶。而从纵向时间上来看,H市近年的房价基本在6000块钱左右横盘,从横向与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对比来看,H市与他们还差一截。
“H市内交通比较拥堵,也是国内比较有名的堵城,地铁房概念肯定能火。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在地铁交汇处,选择流通盘较小的小区,一把吃掉所有的小户型,这样成本低,容易转手,也容易抬起价格。”胡英杰说。
3.G县的卖地“生意”
G县地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西东部,县城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人均月收入2000块钱上下,属于靠山吃山的内陆小县城。当地青壮年多在闽粤两地务工,只有春节时,各地车牌会“云集”县城,之后又冷冷清清。
2011年,江苏“土豪”徐波(化名)来到此地经营设厂,县城一条街道可以从头望到尾,晚上9点过后就一片漆黑。这一年,县财政收入5亿元。徐波属于当地招商引资“圈”过来的大款,到此后不久,G县领导与其渐渐熟络起来。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县领导找到徐波,跟他商议“干出一番事业”。
“县领导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住宅用地每亩大约70万元,你回江苏帮忙找几位开发商过来,下一宗土地招拍挂的时候,必须帮我举牌到250万元以上,超出150万元的部分,县财政会择机返还给你们。楼盘开发后,县里会配合你们把房价炒上去。”一世经商的徐波当机立断,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他很快就从江苏老家招来5个铁哥们。
徐波回忆说,“那块地拍卖那天,起拍价是70万元,从早上8点开始,我们6个人坐在最后排。江西本地开发商每次两千、三千地加价,一路拍到10点钟,我们都快睡着了,才刚刚报到95万元。
眼看着离目标价还很远,我们第一次举牌,报出150万的价码,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们这边。就这样又拍了半小时后,价格还在160万元附近徘徊。眼看着快11点了,我们加快进度,第二次举牌报价230万元,就这样顺利把这块地拍到了250万元一亩。”
这块地后来被规划成G县第一个人车分离地高端住宅项目,2014年开盘价是5500块钱,在当地是“登峰造极”的高价。
徐波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开盘之前,就有浙江游资团队找上门来,答应可以一次性买下三分之一房产,前提是给予内部优惠,每平米降到4200块钱,但对外必须宣称每平米售价6000块钱。
“这是个双赢的交易,开发一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极其庞大,近些年楼市调控日趋升温,房地产项目融资愈发困难,严格时甚至不能拿土地去银行抵押融资,全靠开发商自己解决资金难题,所以财务成本相当沉重,项目开发完成后,如果销售过慢导致资金回笼不了,资金链断裂,就会形成财务危机,更严重就是破产。”
徐波告诉记者,这时候有游资炒房团找上门,就当是薄利多销,解决燃眉之急,先把各种借贷还上,剩下的就可以和当地中介及游资配合,捂盘惜售,统一提价,一唱一和把房价抬起来。如果能再做通当地知名小学的工作,设个分校,那就是暴利的“学区房”项目。
在上述地块拍出一亩250万元的史前高价后,G县又如法炮制出了两个“地王”。这三块地拍出去后,G县县城的房价从3000块钱涨到5000多块钱。财政收入也从2011年的5亿元涨到2012年的8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大概占到4亿元。
“2016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13亿元,其中预算内收入约6亿元,其余的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G县财政局负责人4月1日告诉记者,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当地的工业园基本处于停业状态,鲜有企业开机生产,财政收支压力很大,土地出让也是不得已。
土地财政不仅解了G县的财政压力,也带富了县城周围的居民,依靠土地征迁补偿款,他们在一夜之间暴富。
原先静悄悄的县城,现在夜幕降临后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KTV、酒吧几乎夜夜爆满,当地多位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如今新开的酒店,房间基本都配了一台麻将桌,这些年吃喝嫖赌吸毒的青少年日见增多,看了实在痛心。”

 特稿|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意外离世
特稿|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意外离世 武汉女子一度敲锣救母 今天母亲出院了
武汉女子一度敲锣救母 今天母亲出院了 冠病隔离观察点 泉州酒店倒塌约70人受困
冠病隔离观察点 泉州酒店倒塌约70人受困 杭州失联女童确认遇害 疑点多调查难度大
杭州失联女童确认遇害 疑点多调查难度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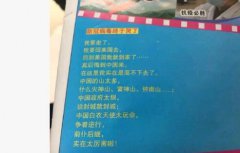 中学生报纸刊病毒诗被轰 主管单位被盗用
中学生报纸刊病毒诗被轰 主管单位被盗用 河南郏县因出现无症状感染者全面封村和小区
河南郏县因出现无症状感染者全面封村和小区 教育部:若达三项要求 中小学可优先开学
教育部:若达三项要求 中小学可优先开学 泉州酒店坍塌事故房主已被警方控制
泉州酒店坍塌事故房主已被警方控制